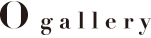“大全(the Whole)不可能别样地存在,因为它只是潜在的,通过活动而分裂……宇宙永远不是給定的(given)。”
–德勒兹,《柏格森主义》 艺术的当代性总是挑起人们对世界中一切“给定性”的反思,不管是自然的还是社会的、材料的还是艺术形式的、人性的还是物性的。孙文佳的作品所关心的,恰恰是如何打破人们对这些“给定性”的迷思,让观众能重新鉴定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观点。《万物归栖》中的作品尝试从材料、艺术形式以至于其探讨的内容,来表现自然和文明、生物和无机物之间的含糊界线,以及其中的演化关系。
对于打破思维中的“给定性”,大漆被选择成为艺术材料并非偶然。艺术家使用这种具备东亚文化传统的材料在当代雕塑中,其用意在于唤起当代艺术观念中关于材料性的讨论。可以说,当代艺术不断深入研究材料与艺术作品所要表达的观念之间的关系,而大漆作为材料无疑则击中了当代性观念的核心,此观念目标为颠倒一切陈词滥调的观点。当众多艺术家们都在寻找和实验后工业社会中各种现成物时(以突破传统材料的枷锁),孙文佳却以大漆进行了一种近乎哲学家齐泽克(Slavoj Žižek)所谓的“精神是一块骨头”(spirit is a bone)式的颠倒。简单说,从杜尚的小便池开始,当代性所要展现的是“精神=骨头”、“非艺术=艺术”、“黑=白”、“传统=创新”的悖论式逻辑,故此它必须颠倒一切常识,却同时一直利用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进行颠覆。孙文佳使大漆脱离“工艺材料”的禁锢,并焕发它潜在于历史中的各种记忆,以至于引起人们对东亚材料及其地域、文化、思想之间关系的回忆和想象。换句话说,大漆如同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的“玛特来娜蛋糕”,让我们重新回到一些被遗忘的片段。因此,作品颠覆的不仅仅是材料自身的“给定性”,其甚至是我们常识中的时间观,如同艺术家德瓦尔(Edmund de Waal)把瓷器看作一道关于时间的谜题(西方近五百年才认识瓷器),孙文佳同样提出了一道关于材料性的谜题——到底这个我们熟视无睹的材料和时间的进程、乃至于自然的变化有何关系?
一旦这道谜题被大漆所抛出,大漆所包裹的奥秘即随之而来。而这些奥秘都体现在作品的造型和艺术形式之中。假如我们认为被大漆所封存的化石所透露的,是先于人类文明的宇宙活动,那倒不如说化石代表了包括人类意识的生命演化。正如柏格森(Henri Bergson)所理解,“物质被描述为生命冲动必须克服的障碍,而物质性被描述为生命运动的颠倒”。作为自然的化石和作为文明的大漆都不过是生命需要穿越的屏障,所以生命运动必须通过颠倒一切物质性来表现力量。今天,我们过于轻易地对人(文明)和非人(自然)划下界线,甚至因而傲慢地视人类文明为一切的中心。对此,孙文佳的作品却真切地通过化石和大漆的结合来颠倒这种被固化的观念,或者可以说生命要冲破的障碍物很多都只不过不过是人类固化的思维。在这个意义下,艺术家的作品仿佛在呼应思辨实在论(speculative realism)哲学家梅亚苏(Quintin Meillassoux)关于原化石(archifossile)的理解,亦即一种不以人和世界的关系为导向来认识世界的契机。如果齐泽克认为“精神是一块骨头”是无限生命的展现,孙文佳的作品则去除了(黑格尔式的)精神这个中项,直接通过艺术形式表达了“生命就是一块骨头”。虽然生命的动力不以人的精神为中心,前者在自我演化并同时让人的意识参与其中。难怪艺术家的大型雕塑作品在模仿脊椎骨节的同时,却扭曲了骨头的形状,其意义在于表现宇宙的生命动力——改变固定的有机结构和功能。正如德勒兹认为培根的画作通过描绘被骨头破裂的肌肉,以达到对“力”的绘画,那么孙文佳则尝试以骨头变形的造型,达到雕刻出“力”的效果。
在此,大漆、化石、骨头、艺术家似乎都成为了生命表达自身的片段,但在这个片段的一刻却折射了大全宇宙的动力,以达到见微知著的生命境界,让我们发现任何“给定性”都不过是幻觉。作品的深意犹如梅亚苏对化石的论述:“古老的化石要求我们追踪思想,邀请我们去发现后者所走过的 “隐秘的通道”,以便实现现代哲学在过去两个世纪中一直告诉我们的不可能性:走出我们自己,把握住本身,了解什么是我们到底是什么”。
–张嘉荣